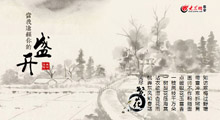新闻热线:0538-8582000
通讯员qq群:40376627
大众报业集团主办
好玉扬名凭借力 泰山研究者周郢为国宝专家揭析泰山玉碑迷踪
2014-04-14 08:09:00
作者: 来源:泰安日报
在泰山玉文化与创作研讨会上,泰山研究者、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周郢向与会专家做了题为《泰山玉碑迷踪》的报告,披露其最新成果,考证今碧霞祠西碑亭玉碑并非乾隆记碑原物,原碑系用和阗碧玉镌制,清末毁于德国侵略者。
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
1、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。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,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 资源转载、复制、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;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,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; 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。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,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。 2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,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,并注明“来源:大众网”。违反上述声明者,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 3、凡本网注明“来源:XXX(非大众网)”的作品,均转载自其它媒体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 其真实性负责。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,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。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,可与本网联系,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。 4、如因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,请30日内进行。
|